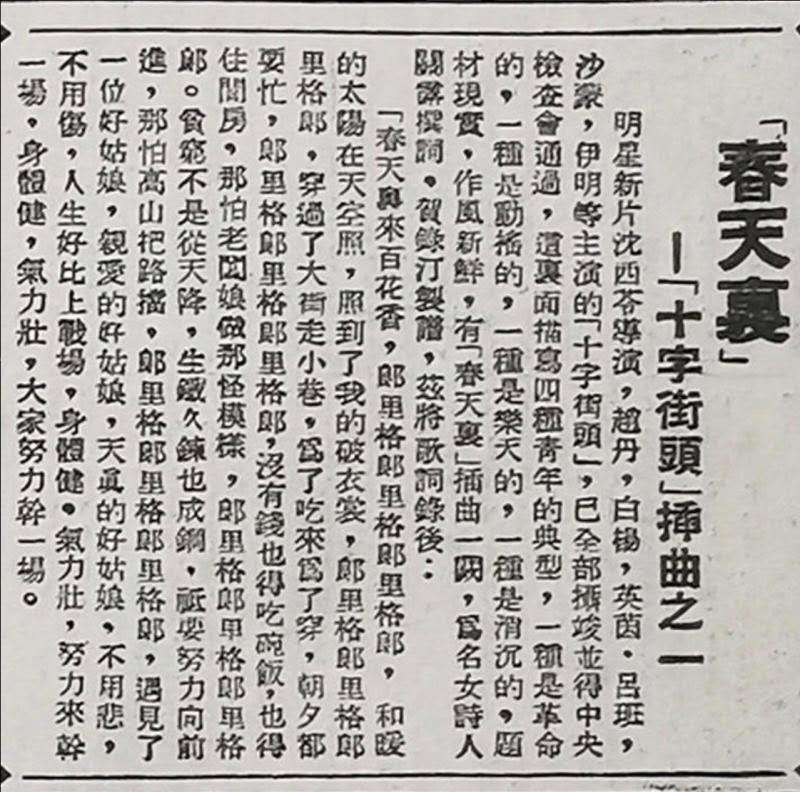迁徙辗转多动荡 包办婚姻誓不从
关露(1907—1982),原名胡寿楣,又名胡楣,出生在山西右玉县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祖籍是河北省宣化县(现为宣化区,当时属于延庆府)。父亲胡元陔是清末举人,在山西省保德、大宁等县当七品芝麻官,为官清正廉洁。关露有个妹妹叫胡寿华,又名胡绣枫,比她小一岁半。8岁时,关露随外祖母去南京姨妈家住了3年,其间在她10岁时,父亲突发急病亡故,此后家庭重担全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
 关露(摄于20世纪30年代)
关露(摄于20世纪30年代)
好在母亲徐绣风从小勤奋好学,曾毕业于南京的女子学校旅宁中学,受过较好教育,有古文基础,还能写得一手漂亮毛笔字,尤精小楷,并工于刺绣。为了全家生计,母亲只能为衙门做“白楷子”工作,即抄写公文,但酬金很少,不得不做些刺绣来贴补家用。当生活难以为继时,母亲只能常常跑当铺……
母亲后来托人在山西省立师范学校和师范附小找到了教语文的工作,生活总算暂时有了安顿。关露11岁时被母亲接回到太原,即到师范附小读书,白天上学,晚上由母亲教古文古诗。在学校里母亲结识了一位姓常的女教师,彼此很投缘,母亲就请常老师与自家住在一起互相照应,叫两个女儿称之常干娘。后来母亲因过度劳累,身体透支,难以坚持工作,便在常干娘的劝说下,于1919年到常干娘的老家湖南长沙乡下去养病。在乡下,母亲曾在一官宦人家教几个女孩子读书,勉强度日。这时关露已小学毕业,就由母亲带教四书五经。关露每天按母亲的布置读书写字,做作文,学写旧体诗。她从不贪玩,不看闲书,学习专一,在母亲的严教与熏陶下,也渐渐爱上了文学。
可是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差,再次病到,两年后还是撒手人寰,此时关露还不足16岁。一家人客居异乡,无生活来源,只得跟着外祖母到位于长沙的外祖母的表侄家寄住,关露称之表舅。表舅家有位中过进士的家庭教师,关露在那里就跟着免费读了一年书。但在亲戚家长住总不是办法,于是外祖母决定带着17岁的关露和妹妹再次来到南京与姨妈同住。
姨妈也是早年丧夫,而且没有子女,孤苦地一人生活。她虽也读过一点书,但文化水平低,仅能看看旧小说,找不到稳定的职业,唯一的财产就是夫家祖上传下的几间旧房,除自住外,多余的出租,她再为鞋店做点鞋上绣花的活计,以维持最低生活。姨妈经常一面喝酒,一面看小说,借酒浇愁,还发牢骚,自叹命苦,埋怨外祖母没有给她找一家有钱人家。
关露就生活在这种贫困又压抑的环境里,但她没有沉沦,因为母亲的言行在激励她:“一个女孩子一定要能够自谋生活,一定要学点本领,否则将一辈子受气,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做人……”母亲的言传身教在她的心里深深扎了根,她意志坚定,求学进取心很强,到处寻师访友,曾到青年会补英文,通过朋友介绍去南京艺专学画……
那时外祖母和姨妈看到姐妹俩渐渐长大成人了,便操心起她俩的婚事了。她们原本都是千余年封建思想的牺牲品,可现在又以封建卫道者的身份自居,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孩的唯一出路就是嫁一个有钱的丈夫,不仅天天唠唠叨叨,而且积极行动,隔三差五托媒人亲友为关露物色好婆家。而关露铁了心不放弃学业,决不服从包办婚姻。几次被拒后两长辈仍不死心,甚至后来关露在上海求学她们也不放过,以外祖母病重为由将她骗回南京,托亲戚为关露物色了一位银行经理。她们想这下该满意了吧,不料也被关露坚决拒绝,这让外祖母和姨妈伤心至极。所以为婚姻事双方矛盾日益尖锐,已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那时军阀混战,烽火连天,南京与其它地方一样也不平静。基于家庭的矛盾和动荡的政局,姐妹俩想到外地避难,但苦于不知到哪儿去。此时长沙的常干娘与她们还有书信往来,时刻关心着关露姐妹俩。1926年冬,正巧常干娘要从长沙到南京来玩,于是就准备带关露姐妹俩绕道上海再回长沙。途径上海时,常干娘正巧通过朋友儿子的引见认识了其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姐夫刘道衡,这为关露姐妹俩走向新的人生打开了一扇窗。
闯申城为革命入党 进左联为救国呼号
刘道衡(1892—1968),湖南衡阳人,早年和大哥刘崧衡一起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刘道衡前往日本留学。大哥刘崧衡牺牲后,刘道衡抱着“兄仇不共戴天”“要报国恨家仇”之心回国。1920年至1931年在上海期间,刘道衡开始研究马列主义思想,积极筹款帮助进步青年办杂志,还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1932年,刘道衡秘密加入共产党,并以民主人士身份周旋政界,为党做情报统战工作,这是后话了。
慈祥厚道、乐善好施的刘道衡听了关露姐妹俩的情况后,表态可以吃住在他家,愿全力资助姐妹俩读书。于是姐妹俩于1927年同进上海法科大学法律系学习,学校里的教师和学生中有不少是革命者和爱国人士,如沈钧儒、史良、李剑华(胡绣枫于1929年与李剑华结婚)等。1928年5月3日,日本鬼子侵占济南,又杀害了国民党政府驻济南特派员蔡公时。全国掀起了反日浪潮,法科大学师生在教育长沈钧儒等带领下上街游行示威,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关露参加了此次游行示威,这是她第一次参与抗日政治活动,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洗礼。1928年暑假,关露考入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文学系,后转哲学系。在国立中央大学,她阅读了古今中外的名著,对中国古代李清照、朱淑贞的诗,和国外歌德、莎士比亚的诗剧尤为欣赏,她本来文学功底不错,在这里得到了进一步修炼。她还经常关注《小说月报》等进步刊物的新作,并且尝试自己写诗歌、散文。这时南京的进步文学青年张天翼、欧阳山、韩起、钟潜九(其中有关露同学)等于1930年初成立“幼稚”文学社团,并在当年3月3日起编辑出版《幼稚》周刊。关露因爱好文学,与他们关系密切,在1930年3月10日《幼稚》第二期上署名胡楣发表了处女作《余君》,由此踏入文学圈。受这些进步同学的影响,她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参加了学生运动。1931年暑期,关露因参与进步学生驱赶女生宿舍指导员事件被国立中央大学开除。这年秋天,她又回到了上海。
认识刘道衡是关露人生的一大转折,由于他的资助,她冲出了矛盾丛生的家庭及封建包办婚姻的牢笼,圆了继续深造的梦,而且贴近了苦难中的中国社会现实。她在两所大学里接触到的进步师生和所经历的事,使她渐渐感到一股革命的激流正在祖国大地涌动,不愿做忘国奴的正义人士正在用各种方式投入战斗,拯救危难中的祖国。
20世纪30年代起,中华民族经历了灾难深重、刻骨铭心的岁月。先是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三省,白山黑水间义旗高举;接着1932年日军又发动“一•二八”事变,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奋起反击;后又爆发1937年“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我国进入全面抗战,抗日峰火遍地燃烧。
在这民族危亡时刻,1931年冬,钟潜九、韩起、张天翼等关露好友从南京到上海找党组织。钟潜九进了法商电车公司当售票员,后到汽车公司当工人,实际是领导工人运动。韩起帮助李剑华(关露妹夫)编辑由刘道衡资助的《流火》月刊,该刊停刊后,韩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关露也义愤填膺,用手中的笔写下了《逃亡者的夜歌》(刊《流火》月刊1931年11月创刊号)及《悲剧之夜》等作品。这时关露由钟潜九介绍,认识了在沪西搞工人运动的胡伊凡,也积极加入其中参加工人运动和抗日活动,并担任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宣传部副部长。其间,关露结识了许多抗日积极分子,其中有一位是在大革命时期入党的纺织厂女工张佩兰,她仔细了解了关露的经历以后,于1932年春介绍关露入党。
同一时期,经张天翼和彭慧介绍,关露加入左联。左联是我党在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领导创建的革命文艺团体,于1930年3月2日成立。它以鲁迅为旗手,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但从成立起就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压摧残。1931年2月7日,柔石等“左联五烈士”被秘密杀害于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左联主办多种刊物,积极倡导左翼文艺创作,培养青年作家,为建设人民大众的革命文学树立了丰碑。
 左联旧址
左联旧址
关露入党后,全身心投入到党的事业中去。她一面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和工人群众运动,一面积极投入左翼文学运动。她的工作是繁忙的,任务也是艰巨的,由此成为左联的中坚人物之一。
关露先是被安排在由丁玲负责的左联创作委员会下面的诗歌组,组里有穆木天、柳倩、艾青等。1933年5月14日丁玲被捕后,创作委员会由关露负责。周扬任左联党团书记后,她担当周扬的“交通”。所谓“交通”,是在当时残酷的政治形势下,秘密党组织为一些领导与相关人“接头”所安排的协调合适的时间、地点等的专属人员,以确保接头任务隐蔽安全。做这项工作要慎之又慎,若有闪失,就会对党组织带来巨大损失。1934年春,她又担任以左联秘书长身份主持工作的任白戈的“交通”。1935年夏任白戈因政治形势所迫去日本,关露再一次担当负责左联工作的徐懋庸的“交通”。连任三届左联领导的“交通”,关露可谓是不畏风险,尽心尽职,得到了组织上的认可和肯定。
关露作为左联成员,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她热心参与各类进步社团,是各社团的活跃分子。1932年9月,她参加了中国诗歌会成立大会。1933年6月底,她参加中华妇女解放促进会成立大会,并作为发起人在宣言上签名;同年参加“苏联之友”社。1935年12月12日,关露在文化界著名人士发起的《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上签名。她还受左联指派去“文学研究社”工作;与沈兹九一起组织女工座谈会等。
1936年2月,因抗日救亡运动形势需要,为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联经党同意自行解散。可关露更忙了:1936年2月16日她参加《文学青年》编辑部召开的国防文学问题座谈会;同年6月7日参加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大会;1937年4月25日参加中国诗人协会成立大会,并被推选为理事。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关露先后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和上海战时文艺协会。11月12日,国民党军队撤出上海,除市区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外,上海均被日寇占领,沦为“孤岛”。那时大部分进步的文艺工作者撤向大后方或香港,有的转移到革命老区,而关露遵党组织指示留下坚持工作继续战斗。1939年2月,她又参加了我党召开的上海诗歌座谈会……
关露始终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她不仅参加众多的进步社团,而且尽自己所能尽心尽力为社团做实际工作,为社团刊物服务,宣传抗日救亡。1933年,她担任《新诗歌》的编辑工作,此刊出至2卷4期时,因组织被破坏停刊,关露日夜奔走,通知已暴露的同志转移,又将存稿妥善保管好;1934年,受左联诗歌组委托为聂绀弩主编的《中华日报•动向》编诗歌副刊;1936年,与一柯共同担任《生活知识》编辑工作,分管文艺类;1937年8月25日,与王亚平创办《高射炮》;1939年,与蒋锡金编《诗人丛刊》……
这期间她还参与了许多其它社会工作:1933年4月应邀去“社联”主办的泉漳中学为进步学生作演讲;关心左联作家的进步,1934年介绍叶紫入党;1936年10月参加鲁迅先生的葬礼;1937年2月随剧组赴南京国民大戏院公演夏衍的《赛金花》……数十年后有作家回忆,当时在社团组织的集会、示威游行队伍里,经常可看到关露忙碌的身影。
但那时关露的生活是艰苦的,甚至是清贫的。她是职业革命者,是作家,但也是一位普通女性。仅靠微薄的稿费收入尚不能维持她的日常生活,她必须要谋生,并以此作掩护。她虽有大学文化水平,中文和英语娴熟,但在当时十里洋场的上海,没有靠山要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谈何容易,更何况还要服从革命的需要和考虑安全等因素。1933年,她好不容易才谋到一份欧亚航空公司小职员的工作,当秘书兼英文翻译,月入75元,这在当时是一份相当不错的收入。但当她知道特务已怀疑她是左联成员时,就立即辞去这份体面的工作,陷入失业。这一时期,她做过学校老师,当过家庭教师、小职员等,也忍受过失业的困顿。由于职业女性的需要,她要穿旗袍、高跟鞋,甚至涂口红,却时常囊中空空,常以阳春面和黑面包充饥,甚至到妹夫李剑华家去蹭饭。
她也常常居无定所,或因革命工作的需要,或为了躲避反动当局的追捕,被迫东搬西迁。据现有资料反映,仅1932年至1938年,她先后至少住过拉都路(今襄阳南路)、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环龙路(今南昌路)、吕班路(今重庆南路)、蒲石路(今长乐路)、拉都路2弄2号王安娜处等。至于临时“避风头”的住所就更多了,如妹夫李剑华家、刘道衡家、赵巷徐鸿家等。
但就在生活颇有压力、居所经常搬迁的状况下,关露面对反动统治的高压环境,心坚似钢,为20世纪30年代抗日救亡运动奔走呼号,为党,为左联,为进步社团作出了常人难以做到的贡献。
左联摇篮育成长 激情创作名声扬
左联是革命文艺团体,作家是要用作品来观照现实、反映时代激流的。
关露是一位诗人,又是文艺写作的多面手,自进入左联后,她的创作生涯总是与革命活动紧紧相连在一起。国难当头,山河破碎,民族的命运、百姓的苦难,时时撞击着她的心灵。熊熊燃烧的抗日怒火、激情满怀的爱国情操,催使她拿起手中的笔,去反映这个危难深重又悲壮不屈的时代,去讴歌那些为祖国而牺牲的英雄们。在20世纪30年代,她一面深入实际干革命,一面用笔挥写这惊雷四起狂飙怒吼的风云。在左联革命摇篮里成长的她,进入了创作的丰收期。
她勤于写作,主要写诗,也写杂文、散文、评论、小说,还翻译国外作品。她的作品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深刻表现了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人民的苦难生活和奋起反抗的决心,无情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求荣的丑恶嘴脸,热情颂扬了中共领导下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
她认为诗歌“是一种强有力的战斗武器”,能“推动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生活的前进”。基于这样的认识,她反对那种无病呻吟、矫揉造作的个人自叹、自作多情,主张诗歌要通俗大众化,能为劳苦民众所接受,并力图在自己作品中作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她的诗作《童工》《马达响了》《机声》《织绸女工》等,一看诗名就知道作者写的是工人和妇女的工作和生活。这些诗富有明快的节奏和音乐性,词汇生动,情感丰富,读来琅琅上口,真实反映了工人们的悲惨生活,揭露了资本家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淋淋事实。
她的代表作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1936年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主要收录了她在1934至1936年间写的精品,掀开了她创作生涯的重要一页。其中如《风波亭》以南宋赵构、秦桧等主和派与岳飞为代表的主战派的矛盾冲突这一历史上已有公论的事实,借古讽今,鞭挞了国民党右翼屈膝投降的反动本质,并以岳飞精神鼓舞人民的抗日斗志。又如《囚徒》,以革命浪漫主义的色彩渲染了对烈士的深切缅怀。那首与诗集同名的《太平洋上的歌声》,更是气势磅礴,铿锵有力,正义的歌声在广阔的空间里传唱,怒吼出被压迫民族的强烈呼声!再如《娜达姑娘》《别了,恋人》《失地》等在叙事、抒情、用词等方面都各具特色。诗集一问世,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奠定了她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女诗人的地位。有文艺家评之为“一位有力的女诗人”,“祈望她在怒吼着斗争的中华民族解放伟大的火线上,锻炼她的武器,获取伟大的收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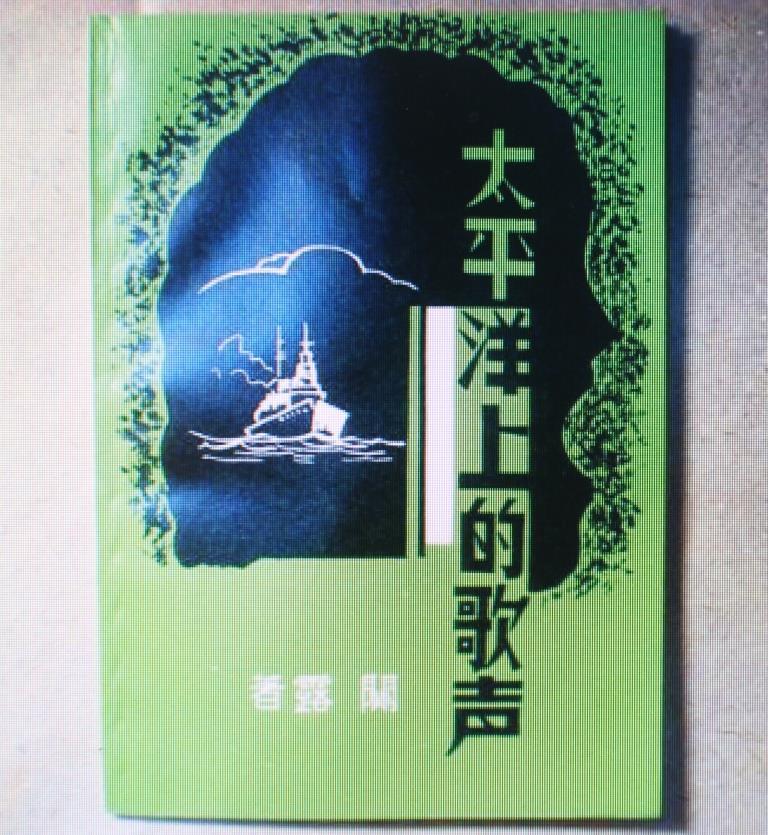 《太平洋上的歌声》诗集书影
《太平洋上的歌声》诗集书影
她写的杂文、散文、评论等,题材广泛,笔锋犀利。有以纪念历史事件来警醒勿忘国耻、鼓舞抗日斗志的《“一•二八”纪念特刊——作家的感情、意见、回忆》《一•二八时候的妇女》《从“九一八”想到我的朋友》等;有专注妇女问题,对爱情、婚姻、家庭方面作深入剖析的《骂人与恋爱》《关于“一杯水的恋爱论”》《诗歌与妇女》等;有对左翼刊物和左翼作品给以中肯评论的《<文艺大路>读后寸感》《<光明>半月刊读后感》《读<未明集>》《读艾芜的<山中牧歌>》等,那是她学习马克思主义和苏联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文艺理论的成果。她的文章深受鲁迅影响,直面现实,富有战斗性,主题紧扣国家民族的命运,字里行间洋溢着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深厚情感。
 关露读田间著《未明集》后的评论文章
关露读田间著《未明集》后的评论文章
(图片源自徐家汇街道与上海图书馆共同举办的“‘星火繁花’——徐家汇红色赵巷主题馆藏文献展”)
她翻译过不少国外的优秀文学作品和进步文章,涉及苏联、美、法、匈牙利等国家。她1938年起学习俄文,一年半后,就将瞿秋白生前未译完的普希金的长诗《茨冈》补译完。在一次朗诵会上她和朱维基、锡金等共五位诗人集体激情地将这首长诗完整地呈现给听众,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她在翻译上的力作是16万字的《邓肯在苏联》。伊莎多拉•邓肯是美国著名舞蹈家,关露崇拜她的艺术才华,同情她的不幸遭遇和悲惨结局,花了大量心血译出了译本,从1936年8月起在《大晚报》的《火炬》上连载,全文16万字,可只连载了8万字就因抗战爆发而停止。译本原稿后由艾寒松带往后方准备交桂林生活书店出版,可又因书店被反动当局查封而未能出版,艾寒松来沪时又将其还给关露。几十年来,关露一直保存着原稿,可惜在“文化大革命”时丢失。
 关露译《邓肯在苏联》自1936年8月16日起在《大晚报》连载
关露译《邓肯在苏联》自1936年8月16日起在《大晚报》连载
(图片源自徐家汇街道与上海图书馆共同举办的“‘星火繁花’——徐家汇红色赵巷主题馆藏文献展”)
她还写小说,短篇散见在《每月文学》《妇女生活》《生活知识》和《申报》《文汇报》等报刊上。1938年起动笔创作的长篇小说《新旧时代》是部自传体小说,自1938年6月20起在《上海妇女》半月刊上连载,边写边刊。小说写的是“我”如何冲出封建牢笼,在革命青年影响下追求自由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作品中有她早期生活的影子,情节上虽没有大的跌宕起伏,然作者对人物尤其是对几个女性的刻画丝丝入扣,加上浓郁的乡土和童趣的描写,让读者有看下去的兴趣。小说反映了封建桎梏下女性的不幸遭遇,抒发了她们挣脱枷锁的强烈愿望,表现了作家对妇女解放的深层思考。作品一问世在上海滩引起不小轰动,后经修改定稿由光明书局于1940年出版。按照关露的想法,是要写自传体小说三部曲的,这是第一部,可第二部《黎明》只写了部分就因各种原因而未能完成。
 长篇小说《新旧时代》书影
长篇小说《新旧时代》书影
关露还涉猎进步戏剧和电影。1936年10月四十年代剧社在上海成立,上演的第一部戏是夏衍的《赛金花》,关露在剧中演小妓女。此剧以辛辣的笔法,嘲讽了国民党右翼投降派还不及一位有人性的妓女。同年11月19~28日,《赛金花》在金城大戏院(现黄浦剧场)公演。1937年2月,关露又随同剧组赴南京国民大戏院公演。
1937年4月,明星电影公司拍摄由沈西苓编导的电影《十字街头》,此片反映20世纪30年代民族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下青年们的苦闷与觉醒。沈西苓特地来到关露住处请她为电影写一首主题歌歌词,要求乐观、活泼、积极向上。关露接到任务即按要求投入创作,写出了歌词《春天里》,由作曲家贺绿汀谱曲。电影上映后广受好评,这首歌也因通俗、清新和节奏明快而流传开来,家喻户晓,“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的歌声传遍街头巷尾,经久不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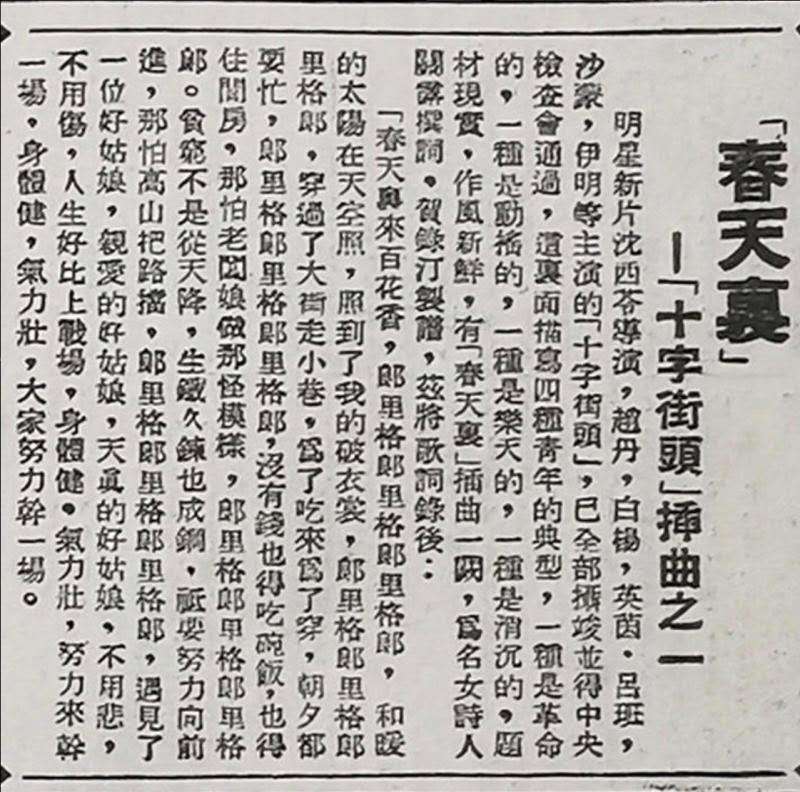 关露为电影《十字街头》插曲作词《春天里》
关露为电影《十字街头》插曲作词《春天里》
(刊《大晚报》1937年3月3日)
在20世纪30年代环境险恶的情况下,关露一面积极投入实践进行革命斗争,一面以多产女作家的身份蜚声上海文坛,写下了许多无愧于那个时代的作品。而她也无愧于作家诗人的称号,是党的方针指示的坚定践行者。
(作者系上海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技术支持:上海江帆网络科技